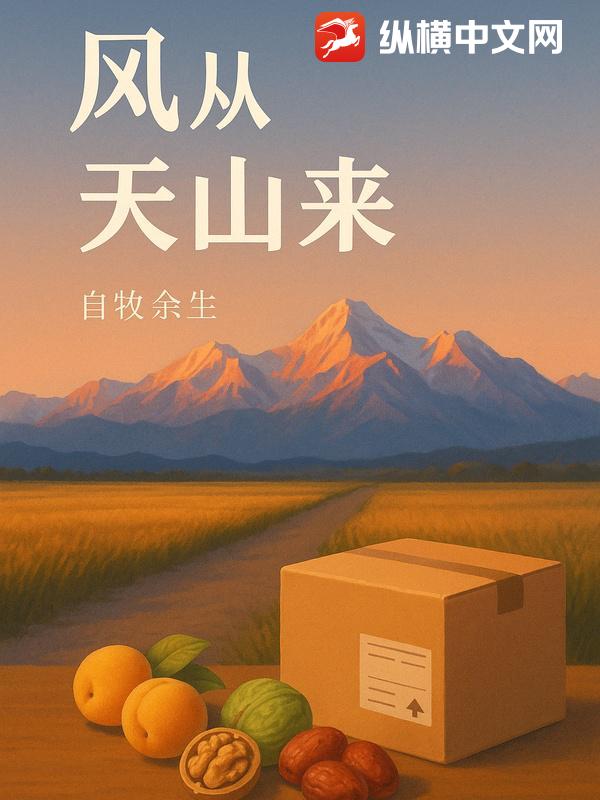###第二十四章线别让人拽断了
李明醒得有点早。
县里的宿舍窗子朝东,天刚透一点亮,楼下的垃圾车就吱呀一声开了过来,像在楼缝里拖一口铁。他摸了摸枕边的手机,六点一刻。群里已经有红点,是“玉尔达工作群”。
他先没点开,起身洗了个脸,灌了两口宿舍里那壶温得有点发涩的开水,才坐回床边,看消息。
最上面是苏蔓的语音,十五秒:“早上好啊大家,昨晚有一家外村的又说要贴咱们的名,我解释了半天,情绪还是有点大,古丽已经安抚了,等你方便的时候回个话。”
下面紧跟着是古丽的文字:“不是大事,就是人家觉得‘你们能卖,我们怎么就不能卖’。我按你说的那套说了,他不完全服气,先让他回去想想了。”
再往下,是吐尔逊发的一张图,还是那台冷柜,温度四度,一如既往,后面还配了八个字:“柜子好好的,放心吧。”
李明看完,心里稳了一半。
其实这种小情绪,他早就想到了。名字打出去了,就不是自己一家人吃饭的事,是整个镇子、甚至外面乡里都盯着的事。谁家要是说“我也想挂”,你不给,他心里就会想:你们是不是瞧不起我们?你要是给了,规矩就得跟着给,一松手,往后就没个头。他在县里呆了这阵,天天听人说“要推广”“要复制”,越听越觉得这事儿像拽一根绳子,左边右边一使劲,真有可能把绳子中间给拽断。
他开了个视频。
那边院子正好开门,光线有点斜,能看见大门口那条被风常年蹭得发白的门槛。古丽穿了件浅色衬衣,头发扎得高高的,人站在门口说话,就像在给谁交接班似的:“醒啦?”
“醒了。”李明笑了一下,“我这边还没上课。说说,昨晚什么情况?”
古丽把手机调了个角度,镜头里能看见院子里靠墙堆着的几箱核桃,还有昨天刚写的那张白板。她说得不急:“就是我们西北角那个村,叫来了个亲戚,说他家也有核桃,也晒得好,他想也用‘玉尔达’这个名。按理说他家核桃也不坏,但是他没走我们的检验,也没在服务站这边开个档,我就说‘要用咱这个名,可以,得按这个来’。他就不高兴了,说‘都是一个镇的,凭什么你们说了算’。”
“他是你说的那个,平时来集市上卖刀子的舅哥?”李明问。
“对。”古丽点头,“人不坏,就是脾气有点直。再说他还带了个外甥女来,面上也不好驳得太死。我就说‘回去想想,明天你要是能按这个写单子、贴条子,我们就替你卖;你要是不想按,我们也不拦你卖你自己的名’。他没说话,走的时候脸还是有点绷着。”
“嗯。”李明听完,手里转着一支笔,心里已经在过那条老路了,“你跟他说得对,就得这么说。他要是真心想跟着走,明天自己就回来了;要是不想,他今天上午就会在村里说‘他们不给我贴名字’。到时候我们就要出一个公开的说法,把这个口堵住。”
他想了想,又问:“苏蔓呢?”
“她在屋里做图。”古丽回头喊了一声,“苏蔓,李明来了。”
苏蔓端着个杯子出来,手里还是捏着手机,一边喝水一边说:“我就等你这句话。要不要我今天就做一张图,写‘想用名字的,必须走服务站’?”
“别写得太硬。”李明说,“写得像提醒。比如——”他眯了下眼,想了一个调子,“比如说‘为了让买东西的人放心,我们统一在服务站验货、贴条,再发出去。大家有好东西,先送到站里,我们一起卖。’这样好听一点,也不容易让人觉得咱们是故意卡他。”
苏蔓连连点头:“行行行,我一会就做,你看不看?”
“做完先给古丽看。”李明说,“她这两天站在第一线,她说能说得过去,那就能说得过去。”
说到这,院子那边忽然传来一阵笑,是买买提江开车进了院子,车头一歪,车上还拉着两只塑料筐。他一看是李明,冲镜头挥了挥手:“你们县里舒服不舒服?”
“还行。”李明笑,“你车稳不稳?”
“稳着呢。”买买提江说完就去卸车了。
画面晃了一下,古丽把手机拿回到自己面前:“你会儿还有课吧?”
李明看了看时间:“有,九点半开始。不过我这边也差不多说完了。你们院里要是有人来问,就按咱们刚才那句话说。必要的话,多说两遍。”
“好。”古丽说,“你忙吧。”
视频挂断,宿舍一下子静了下来。李明坐在床沿上,想起昨晚写到一半的那张纸——他在上面写了八个字:“名字要留住,口子慢慢开。”这八个字说难也不难,说容易也不容易。留住名字,是说这个“玉尔达”不能变成谁都能拿去用的;口子慢慢开,是说真要带着周边村子往上走,也得开,不然人心迟早要起刺。最要命的是,这两句话说起来是一个人能决定的,做起来却不是一个人能定的:上面要推广、下面要跟着吃肉,中间又要留一个最初的味道,这事儿就是两头同时使劲的事儿。
他把那张纸折好,夹进了文件夹,这就出门去县委党校的教室了。
这几天的培训班其实不算烦。坐在下面的都是各乡镇推出来的年轻人,或者是那些镇上做得不错的女干部、会说普通话的老乡,一眼看过去,都是已经干过点事的人,不是那种一上来就说“我啥也不会,教我”的。他们上来就问:“你们怎么让老乡相信你们不是搞形式?”“你们那个退款怎么做到的,老乡没吵?”“你们那边有冒牌的了,你们怎么处理的?”一问就知道,人家是真的在做。李明也不藏着,能说的都说,不能说的,就换一种说法:“这个要看你们那边书记怎么定,只要大家说法一样就行。”
不过今天不一样。
今天在后排坐了俩镇上的副镇长,一男一女,都是三十多岁,穿得利利索索的。男的开口就直:“李明,我直接说啊,我们那边村民也问过我,为什么你们‘玉尔达’能卖,我们就不能卖?你们是不是把好东西都留给自己了?你看你们视频里说得可好听了,说‘我们这个镇的’,那别人镇的呢?”
一下子就问到要害上了。
教室里顿了顿,前排有人回头,有人低头写字装没听见。李明看着那副镇长,没急着说。他知道这种话可不能一句顶回去,这要顶过去了,回去人家就得说你“在县里不给我们面子”。
他笑了一下:“我要是真想全部留我们镇,我就不用来这儿讲了,对不对?我就关起门来卖了,反正我们这几个月也卖得挺好。可是我们来这儿讲,是想把这条路说出来,让大家一起走。只不过走的时候,总得走得稍微齐一点。”
那副镇长还想说,坐在一边的周科长咳了一声:“小吴,你让他把话说完。”
李明接着说:“我们那边为什么先走起来?因为我们有人在这儿天天盯着,老乡送来的东西,我们一箱一箱看,我们说‘这个不能发’,我们就真不发。你们要是也能做到这点,谁会拦着你们用这个名?咱们一条街上的铺子,哪家做得干净,客人就爱去哪家,这是一个道理。我们现在把规矩都写明白了,大家要用,就把规矩拿走。名字——”他顿了顿,挑最关键的那句,“名字我们想留住。留住不是不给你们用,是怕以后这个名字说出来,老乡问‘你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’,咱们答不上来。要是全县都一个名字,那就全县都要做到同一个标准。这个事儿,是难在这儿的。”
他说完,教室里没人说话。
坐在后排的女副镇长倒是点了下头:“我听懂了。你们这个名,是你们一筐一筐看出来的。我们要想用,也得一筐一筐看。”
“对,您说的这个最对。”李明赶紧接,“我最怕的就是,过两天县里一宣传,说‘我们这个县都叫一个名字’,结果下面有的镇没有人看货,直接往外装。那到时候出点事,外面骂的不是你们那个镇,骂的是这个名字。那你说,我们这几个月不是白忙活了?”
周科长在前面轻轻点了点头,像是给他做了个记号:“这块我给你说一说。”他转头对大家说,“今天这个话你们都要记一下:名字是个招牌,招牌不是非要统一成一个样子才算统一。有时候你们觉得统一,其实外面的人看着是乱的。咱们回去跟县里说一声,‘县里甄选’可以有,但是哪个镇的,也要写清楚,比如‘玉尔达甄选’,‘阿依库勒甄选’,这样大家都看得懂。”
有了这句话,李明心里才算松了一点。
散会的时候,那个男副镇长还是走过来,态度也不冲了,只是叹了一句:“唉,主要是我们那边也等着吃这口饭呢。你说他们看你们卖成那样,能不眼红吗?”
“能理解。”李明拍了拍他胳膊,“你要真想干,我回头把我们那几张表拿给你,照着做。你要是嫌麻烦,你就让人家先走。说白了就是这几句话。”
对方“嘿”地一声笑了:“你这个人,说话还行。”
“那是。”李明也笑,“不然我们那几个妇女能听我的吗?”
说完人都散了,教室里只剩下一股粉笔味。李明把黑板擦了,心里想着玉尔达那边的事。
他知道,今天上午镇上那家亲戚肯定会在村里说话的。说“他们不给我贴名字”。说“他们嫌我们东西不好”。说“人家就是看自己镇的”。这种话,在乡里像风一样,一会儿就会吹到每个人耳朵里去。吹得久了,就有人信。有人信,就有人起头来闹。他不在院里,就得提前把这种风折到地上。
午饭过后,他刚回到宿舍,手机就响了,是古丽。
“喂。”
那边声音有点低,听上去是在院子里背着风说话的样子:“我跟你说一声啊,他果然在村里说了。我表妹在那边,刚跟我说有人在群里发了‘他们不给我们贴名字’的截图。”
“我就知道。”李明坐到床上,“下面咋样?”
“还好。”古丽说,“我们这边的亲戚都替我们说话,说‘他们不是不给,是要你走顺了’,说‘你昨天不也听了嘛,他说先送到服务站嘛’。大家嘴还挺一致的,就是有两个人说了一句‘他们现在翅膀硬了’。我没回。”
“你不用回。”李明说,“你要一回,就变成你跟他们吵了。”
“我没回。”古丽顿了顿,声音慢了下来,“李明,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啊——我现在才知道你平时在院里有多累。你不在,我一天要解释好多遍。都是同一句话,我要对小孩说一遍,对老头说一遍,对爱较真的媳妇说一遍。我都说得头疼。”
“这就对了。”李明笑出声,“你要是一天一句话都不用解释,就说明这个事儿已经不热了。你想想,之前咱们刚开始收杏子的时候,我一天解释多少遍?”
他本想说“杏子”,说到一半想起你说过的不让再提,就换了一句:“就是刚开始收那茬鲜货的时候。”
古丽也笑:“行,你说得对。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,我没乱。”
“你肯定不会乱。”李明说得肯定,“你要真乱了,我也得回来了。”
说到这,两人都没说话,电话里只剩下一阵风声。好像院子那边有人在搬箱子,塑料箱子和地面蹭了一下,声音干干的。
古丽忽然说:“对了,晚上你有空不?苏蔓说要拍一条‘怎么把自己村的东西送到服务站’的视频,她说你要是在,我们三个人说一段话,比她自己说好。”
“晚上我这边有个小讨论,估计八点多才能回宿舍。”李明想了想,“要不你们先拍,发给我看,我看完给你们说说哪里要改,再发。”
“行。”古丽说,“那就这样。你注意别太累。”
挂了电话,李明靠在床背上,长长呼了一口气。
其实他也累。
这几天县里天天有人来找,说“李明,我们想看你们那个白板”“李明,你们那个唛头给我拍一张”“李明,我们那边乡长想跟你加个微信”“李明,县里想让你过两天讲一下那个‘公开查验’的细节”……全是这种听上去不麻烦、加起来就很麻烦的事。他本来想,来县里这一阵子,可以稍微歇一歇,结果根本歇不了。院子那边的风吹到县里来了,县里这边的风也要往院子里吹。两边都是风。
他翻开笔记本,把上午那件事记在上面:“外村要贴名——解释一次——发统一图——周六开放日”。后面又写了六个字:“让他们看一眼。”
对,得让他们看一眼。
不让人看,人家就会觉得你是在藏着掖着。让他看了,哪怕他回去还是说“不服”,那也没关系,大家都看过了,院子里的人知道你没有搞小动作,风也刮不起来。
想着想着,他又想到自己父亲。
当年在县城修那条路的时候,也就跟他现在一样——上面下了指示,说这段路要平,要宽,要能跑车。结果下面的村子就来了,说“我们能不能多修两米到我们村口?”“我们这条沟能不能一块儿修?”后来他父亲跟他说过一句话:“修路的人啊,最怕的不是多修,是这头那头一块儿喊,你只能选一个。”当时他还小,只觉得父亲说得像谜语。现在明白了,一条路要走得远,就得有个主干。你要是每个分岔口都说“这也行那也行”,这条路最后就像河漫滩,哪都能走,可哪也走不深。
他正在发呆,门被敲了两下。
“进。”他说。
周科长探头进来:“在呢?”
“在。”李明赶紧站起来,“科长您坐。”
“坐什么坐。”周科长把手里的文件夹往桌上一放,“刚才我去了一趟县里那边的会,跟你说一声,上面那个名字的事儿,我帮你说了。大体意思是可以有一个‘县里甄选’的大名,但是下面的镇名必须写。你们这个‘玉尔达’三个字,保住了。”
李明心里“咯噔”一下,是真松了口气:“那就太好了。”
“不过啊——”周科长一屁股坐在他床上,压得床板“吱呀”一声,“上面还是说了,他们既然想搞这个县里的一张皮,就不能只你们一家人漂亮。到时候县里要搞个小小的现场,就在你们那个镇开,叫周边的乡都带点东西来,你们给他们示范一下,你们也别嫌烦。”
“我们不嫌烦。”李明说得很快,“只要名字能留住,别的我们都能配合。”
“我就喜欢你这句话。”周科长点头,“你们这小年轻,嘴不硬,事也不赖,这个事情就能谈。你要是上来就说‘我不行’,我也没法在上面说话。”
“明白。”李明说,“这是咱们一起的事儿。”
周科长站起来,把衣服往下一理:“行,那我就不耽误你午休了。晚上那边的材料你写好了发我,我看一眼给你批个字。”
“好。”李明送他到门口。
门一关上,屋里又安静了。李明伸了个懒腰,低头看了一眼手机。群里已经有了新动静。
苏蔓发了一版图,背景是院子门口那块蓝色的大门,字不多:“老乡的好东西,先送到站里,我们一起卖;大家的名声,一起护。”底下还加了一个小小的“玉尔达甄选”字样,和他们的头像一模一样。
古丽回了句:“行,就发这个。”
买买提江紧跟着发了个大拇指。
吐尔逊发了个“OK”的手势。
李明就没再说什么,只点了个赞。他知道,他们在院子里已经能自己对上节奏了,他不需要再一条条去说。
晚上,玉尔达那边果然围了一圈人。
这次不是来看检查的,是听说“可以带东西来问一问”的,大家都想来试试。古丽站在门口,脚边摆了三四只筐,里头都是核桃、枣干,还有两袋巴旦木。她把人一波一波往里放,一边说:“你们的东西都不差,就是得有个顺序。咱们这边先把这几样卖稳了,往后再带别的。你们要想用这个名字,就按这个走。不想用也没事,咱们不拦你们卖自己的。”
有人问:“那我们要是想自己开个账号,能不能写‘玉尔达附近’?”
古丽笑了:“你这个还行,比那个直接写‘玉尔达’的强点儿。不过我们还是建议,大家都走服务站,大家一块儿有个样子。你看,我们也不是不给你们机会,你们今天不就来到这了嘛。”
一旁的苏蔓拿着手机拍,拍完就发了条短视频:“今天来了好多附近的乡亲,大家都说东西好,我们也想一块儿卖。欢迎大家送过来,我们一起把它卖出去。统一贴条,统一说法,大家都好办。”
这条视频发出去,评论区很快就有了回应:“这样说就明白了”“早说要走服务站嘛”“就怕有的人走后门”。也有个别的说“名字早晚要一块儿用”。但这种声音不多,很快就被下面的赞同淹没了。
李明躺在宿舍的床上,看着这一幕,心里觉得很踏实。
他知道,这一章小风算是压住了。真正的大风,还在后面——等县里那一批镇都学完了,也都想“用名字”的时候,这条线还得再拉一次。但至少今天,他没有让它断。
天黑得快。县城的风没有玉尔达那边那么干,吹在脸上有一点水汽。宿舍楼对面是一条铁路线,晚上会有一两辆慢车过去,声音低低的,像是天山那边的风绕了一大圈才到了这儿。
李明坐在桌前,把手里的笔又拿了起来。
他开始写明天要交给周科长的那份《玉尔达模式往下放的建议》。他没有用什么好听的官话,就跟平时记笔记一个样儿,一条一条往下写:
一、名字不动,外面加。
二、规矩先讲,再让人上手。
三、东西能不能卖,得让本地人说了算。
四、出问题了,站里的人要站出来。
五、能做到的再承诺。
写到这里,他想了想,又补了一句:“这事儿急不得。”
他写完,放下笔,揉了揉眼睛。
窗外有风吹过来,吹得窗帘轻轻动了一下。他忽然想起了玉尔达的那堵白墙,想起了院子里那口老井,想起了吐尔逊店门口总是呼啦啦的风,想起了买买提江总爱说的那句玩笑:“车稳,人就稳。”
是啊,车稳,人就稳。
他把本子合上,心里默念了一句:别让这根线让人随手一拽就断了。哪怕两头都在拉,也得让它还能扛一扛。
然后他关了灯,屋子里一下子暗下来,只剩下窗帘晃动的影子。远处的火车慢慢过去,声音压得很低,像一条从天山那边吹来的风,过了玉尔达,又过了县城,还要往更远的地方去。